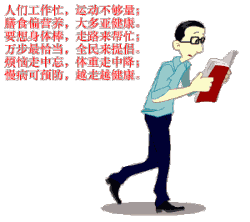Ciro de Quadros曾领导过公共卫生史上最成功的一些免疫运动。他告诉Fiona Fleck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今天比过去更难消除疫苗可预防的疾病。

问:您是怎样开始对免疫问题感兴趣的?
答:19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我在亚马逊地区一个小城镇的卫生保健中心里工作。之后学习了流行病学并加入了一个新建的国家流行病学中心,某种“巴西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但这个中心从未启动,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军事独裁政府指控为共产党人。我则通过该中心,在巴西开始参与天花运动。
1969年,我和其他三名同事一起对监测和控制战略进行了最初一些尝试。巴西的天花规划以大规模疫苗接种为基础,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每个州进行大规模接种。因此我们选择在四个州建立了监测和控制单位。我是巴拉那州单位的负责人,这个州约有800万人,我们在7、8个月内确认了1000多例天花病例并为其接触者,约3万人接种了疫苗,由此阻断了传播。我们在该期刊上公布了这项研究。这是我开展免疫规划的首次经历。
问:什么是监测和控制?您是怎样帮助制定这个方法的?
答:巴西的天花规划始于1966年,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目标是为每一个人进行接种。但当Donald A Henderson前往日内瓦担任世卫组织消灭天花规划的负责人时——那是在我开始天花工作之前,他和他的团队认识到一些疫苗接种覆盖率高的国家也仍然暴发天花疫情,而且大规模疫苗接种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有效。他们知道天花患者脸上有痘疤痕迹,这些人通常知道自己在哪里遭受感染,因为他们曾看见别人也这样。他们说如果能沿着传播链从一个患者追踪到另一个患者,追溯几代人并为与天花患者有接触的所有人接种疫苗,那么便可以阻断传播链。
这便是监测和控制战略的运作方式。在巴西,监测和控制经证明是项很出色的战略,并在西非和印度的研究工作中得到检验,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正是因此,这成为了全球天花规划的最终战略。
问:如今巴西正努力填补偏远地区的医生职位。是什么促使您去这些地区工作?
答:当我申请到国家公共卫生学院学习时,那里的一名教授建议我首先去实地工作。一个名为特殊公共卫生服务的基金会当时正在巴西偏远地区开展活动,需要医生。他们派我去亚马逊地区领导一个卫生中心,该中心位于帕拉州一个叫阿尔塔米拉的城镇,居民约4000人。我们的全部人员包括一名社区护士、一名实验室技术员、一名公共卫生人员和一名行政人员,要照护该城镇居民的健康。
疫苗覆盖率不是很高,大概约50%或60%,而我们只有少量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百白破疫苗)、破伤风菌疫苗和[抗结核病的]卡介苗。1970年代初,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情况都类似。但我们的小团队在我领导的头一年中依然设法将覆盖率提高到近100%。
我们确认了该城镇的传统接生员,他们每周来卫生中心一天,汇报各自地区的出生情况,我们对这些情况几乎100%进行记录,然后给他们一些消过毒的材料,在以后接生时使用。我们有良好的记录和跟踪系统,如果孩子不来接种第二剂或第三剂疫苗,我们的护士或公共卫生人员会去家访,以确保为孩子进行接种。我们还派公共卫生人员去居民家中修建厕所和连接供水设施,以改善环境卫生。
问:今年是扩大免疫规划四十周年。1977年时,您到泛美卫生组织工作,在美洲启动了该规划,您是怎样开始的?
答:世界卫生大会于1974年批准该规划后,三年没有任何动静。疫苗接种覆盖率极低,发展中世界许多地区不足10%,大多数国家只使用三种疫苗——百白破疫苗、破伤风菌疫苗和卡介苗。美洲区域多数国家甚至没有免疫规划,只是在应付疫情。我的任务是帮助各国自己进行组织安排。首先,我们要求它们任命一名免疫管理人员,负责运行其规划。它们在一年内做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培训这些管理人员,使其随后能够训练自己的工作人员。
问:1994年,美洲是第一个经认证无脊灰的世卫组织区域,2002年以来,又在控制麻疹。为什么扩大免疫规划在美洲区域如此成功?
答:我们举办会议向各国介绍扩大免疫规划的概念,很快所有这些国家都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将所有国家管理人员以及从事流行病学、初级卫生保健、孕产妇和儿童卫生、筹资等工作的其他政府人员召集起来并询问他们:“你们在自己国家努力实施免疫规划时都遇到哪些问题,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我们将有关问题罗列出来,包括如何提高覆盖率、如何进行监测和组织冷链等,并对它们进行分析。
之后我们编制了一份出版物,题为《免疫和初级卫生保健:问题与解决办法》(泛美卫生组织科学出版物第417期),同时就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开展工作。泛美卫生组织今天仍在这样做。
问:您在扩大免疫规划的最初几年中受到批评,您是怎样战胜这些批评者的?
答:1979年,在泛美卫生组织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哈夫丹•马勒博士告诉我他再也不会让天花这样的规划在世卫组织工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当我们于1985年在美洲启动消灭脊灰规划时,他却给予了支持。在头三年中,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战略在阻断脊灰传播,这促使世卫组织内部发出呼吁要在全球消灭脊灰。1988年在法国塔卢瓦尔举行的会议促使卫生大会通过了消灭脊灰的决议,马勒加入了其它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各国卫生部长的行列,大力支持消灭脊灰。
问:八十年代中,美洲扩大免疫规划受到武装冲突的威胁。您是怎样应对的?
答:十年内战期间我们遇到许多安全问题。我们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秘鲁和其它国家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努力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它伙伴合作并试图与冲突集团达成解决办法。我们幸运地在交战各派之间促成了一些和平的日子。
第一个日子是在1985年,萨尔瓦多。那天,包括游击队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参加全国免疫日活动,这一天成为所谓的“宁静日”。当时的泛美卫生组织领导人[Carlyle Guerra de] Macedo博士称此为“和平之桥梁”,因为我们通过讨论卫生问题克服了难题。今天,尼日利亚,特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比拉丁美洲更加复杂。我知道全球消灭脊灰行动正在对付这些问题,而这并不容易。
问:扩大免疫规划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答:我们于1985年启动脊灰运动,1991年在美洲发现最后一例。目标原本是1990年,我们晚了8个月。我们没有鼓励开展相互独立的规划行动,像你们今天在全球看见的那些。例如在扩大免疫规划之外开展一项全球消灭脊灰行动或在规划之外独立运作一项麻疹和风疹行动。我们则尽可能将针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所有规划整合起来。
所以,国家脊灰运动包括麻疹疫苗、百白破疫苗和破伤风菌疫苗等其它一些疫苗。许多国家极其热衷于消灭麻疹,以致在脊灰运动期间设法控制麻疹,有些甚至阻断了麻疹传播。我们说:“现在不要这样做,首先要完成消灭脊灰的工作”,但有些国家就是意欲消灭麻疹。
问:您的意见是什么?
答:避免各自为政。目前在同一领域有太多的行为者: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必须要使它们全都协调一致。还有,随着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出现,另一个重要挑战是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疫苗提供资金。这些国家负担不起昂贵的新疫苗,但却没有像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样的组织来帮助它们。制药业在试图划分世界,它们的分级定价策略具有破坏作用,因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负担不起这些疫苗。
需要有新的机制来提供这些疫苗,如创立于1979年,如今已拥有约1亿美元资本总额的泛美卫生组织周转基金,同时可通过批量购买使价格降低。
问:您是脊灰独立监测委员会的成员,过去曾领导《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工作。为什么疫苗十年和《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进展缓慢?
答:《全球疫苗行动计划》是一项了不起的倡议,但后续工作不力。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有必要编制或确定各自的“区域疫苗行动计划”,同时各国需要获得支持以编制其“国家疫苗行动计划”。必须克服实施方面的各种障碍,如预算拨款不足和伙伴之间缺乏协调等。
问:为什么会延迟?
答:首先需要将《全球疫苗行动计划》转变为区域和国家疫苗行动计划。例如,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非洲扩大疫苗规划管理人员会议上,我问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两年前批准的,作为区域和国家模板的《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结果“无一人”读过,因为他们对该行动计划显然不太知情。现在已经进入疫苗十年的第四年了:我们必须加快进度。世卫组织必须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问:您职业生涯中的什么经验对您的工作影响最大?
答:消灭天花规划的各种经验教训至今一直伴着我:这就是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人人都要理解这个目标,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必须长期持久地进行研究并向实地提供反馈,而且必须获得资源和政治支持。这些是我们带给扩大免疫规划的原则,也是我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生涯中的经验。
问:有什么事您现在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
答:没有。我很高兴参加了那么多重要的行动,同那么多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我至今的历程十分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