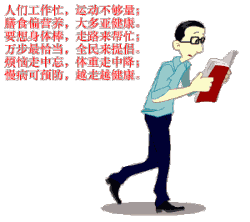寒冬腊月,身穿一条防风皮裤,耳戴蓝牙耳机,骑着摩托车在黄土高坡上风驰电掣。这就是贺星龙多年来留给乡亲们的典型印象。他岁数不大,只有36岁;学历不高,职业中专毕业;工龄不短,已经当了16年村医;名气却很大,在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乃至与大宁县隔着一条黄河的陕西省延长县,方圆几十公里的许多人家都保存着他的手机号码。
■卫校毕业后选择回到农村
近日,在贺星龙的卫生室,他向记者展示了十多年前他在徐家垛乡“七沟八梁”间穿行的照片。照片中,他咬牙挑着一副扁担,两头挂着药箱,荒草淹没膝盖,汗水浸透衣裳。多年前,当村里各家各户借钱给他前往临汾市读中专时,他的梦想是借此改变命运,离开农村在城市扎下根来。
在读中专时,贺星龙改变了想法。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乐堂村当一名村医。
大宁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徐家垛乡是大宁县有名的贫困乡。贫困的根源在于自然条件恶劣。有一技之长者或者年轻人,纷纷外出。“比如乐堂村,全村有户籍人口540人,常住人口只有200多人,都是留守的老人以及父母离异的孩子。”徐家垛乡卫生院院长孙全富说,徐家垛乡有15个行政村,很多村医都七老八十了,没有退休制度,更找不到人顶替,贺星龙是村医里面最年轻的。
这是时代的困境,16年前,贺星龙迎面走了进去。刚毕业时,一位创业成功的同学劝他到省城太原加盟医药营销,一年能挣四五万元,贺星龙谢绝了。他的想法很朴素:“我上卫校学医是乡亲们凑钱供的,我要是毕业了留在城里,感觉对不起乡亲们。”
■24小时上门服务
2000年,贺星龙回到了村里,可要行医看病,却连最起码的听诊器、血压计都没有。了解儿子秉性的父亲,把住的窑洞腾出来作为诊所,自己住在危窑里,并且狠心把家里仅有的两只母羊卖了,加上卖玉米的400多元钱,买回来几件必用的医疗器械。
接着,贺星龙就印了4000张宣传页,发到周围的村里,郑重承诺:病人就是亲人,电话就是病情,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他还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设置成了手机的彩铃。为了治疗一位被大医院连续下过3次病危通知的老人,他曾半个月没回家,在老人床前的椅子上度过15个日夜。老人的病好了,打电话找他看病的人更多了。
随着病人的不断增加,靠挑着扁担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贺星龙终于攒够钱买了摩托车,这些年,他前后骑坏了6辆,跨越陕西、山西两省的28个行政村,行程40多万公里,上门为留守老人、孩子看病。“忙的时候,几乎每个小时都有电话打过来。”贺星龙说,“为了方便骑车时接电话,我又买了蓝牙耳机。”
在乐堂村,85岁的张力山与84岁的老伴相依为命,唯一的儿子在县城工作。老两口长期患有肺心病,一旦发病,首先想到的便是给贺星龙打电话。记录着电话的名片被夹在土窑门口的镜框里。“这样方便看。”张力山说,贺星龙随叫随到,“听到他的摩托车停在院子里,心里一下就感到安稳了”。
贺星龙作为农村中“稀缺”的年轻人,不仅坚守在村医的岗位上,同时更像是这些留守老人的子女,在生活起居等方面提供帮助。张力山说:“有时候犯病需要住院了,贺星龙就会帮忙联系车辆;家里一些重活干不了,也经常请贺星龙帮忙。”
贺星龙拥有全村唯一的一台电脑。这台电脑是大宁县卫生部门给他配备的,通过网络,贺星龙将村里的疫情信息、治病诊疗情况、公共卫生服务统计报表传送出去,同时也在一些知名医学网站上浏览信息。“做村医还是要多学习,比如如何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农村就特别有用处。”贺星龙说。
■坚持下去需要更多保障
根据大宁县的统计,在全县医务人员队伍中,乡村医生群体问题最为突出,大部分年龄偏大、素质偏低,60岁以上的村医占32%,因为懂电脑的不多,除了坐诊之外,几乎做不了公共卫生服务。
贺星龙是这群村医中的“另类”。通过电脑,贺星龙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发生快速的改变。眼见着以前的同学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他所面临的家庭压力也越来越大。2009年,他的两个孩子到县城上学,由于没钱租房,妻子只好找了一间离学校较远、即将拆迁的危房暂住,周围垃圾遍地,屋里走风漏气。妻子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一间门面房,打算逼迫贺星龙到城里行医。可贺星龙没有同意,夫妻俩唇枪舌剑后,对峙了两个月,最终还是妻子妥协了。
如今,贺星龙与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在县城陪孩子上学,兼职给人打字,一月有七八百元的收入;贺星龙坚守在村卫生室,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七八百元,家庭经济开支还需父母种地补贴。
在贺星龙家,记者发现7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载的全是近4年患者赊欠医药费的账目。“以前的账本,我已经全部烧掉了。”贺星龙告诉记者,“村民生了病,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他看吧?”行医16年,贺星龙为13个五保户支付药费45689元,赊账、死账57235元,自己至今还背负着2万多元的债务。
最近,贺星龙听说大宁县卫生部门正在研究给像他这样年轻的村医更多扶持。他感到很高兴,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村医这份职业如何坚持下去,需要更多的保障。□健康报记者 叶龙杰 特约记者 郝东亮□